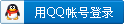除夕随笔
除夕随笔
除夕的不同在于它是一年中最后一天,生肖更迭,人们也在这个夜晚又长上一岁。除夕夜要做的事情很多吧,比如包饺子、看电视、祭天地、祭先祖、年夜饭等等。
昨天和爱人商量,午后的菜不宜做的过多,四菜一汤足矣。一家三口人,小孩儿吃得不多,我有胃病也吃不多,爱人的饭量有限。但她还是坚持做了八个菜,说要么六个,要么八个,数字吉利。饭后小睡一会,养了养神,爱人则略微休息一下,忙起包饺子的事情。我说要芹菜馅和韭菜馅的,也是取“勤”和“久”的意思。每到重大的节日,中国人就喜欢用这些文字来表达美好的祝愿,也算传统吧。
女儿去年还对闪烁的彩灯拍手跳跃,对挂在墙上的大鱼充满新奇,让我真正体味到她的快乐从而感到这个年的意义,今年她已经对我忙碌着布置房间没什么兴趣了。她一如既往地和沙发上那群动物玩偶们为伴,教他们学习,指挥他们列队,偶尔还严厉地指着其中的狗熊或者米老鼠大加批评。那些玩偶们的确可爱,尤其是熊,如果你抱一个在怀里,对着它的眼睛看,会感到它也一样憨憨地看着你,特别可爱。难怪女儿一直爱着它们。女儿玩她自己的,我觉得轻松不少,若不是那么多拜年短信要回复,恐怕也无所事事了。
看着春晚,多少有些木然。春晚将2008年一年的大事梳理了一遍,唯有灾区的代表们上来,让我涌出泪水。苍天一度把我们的幸福无情撕碎,给我们看,地裂山崩,房倒屋塌,同胞逝去的生命,如一把利刃在心脏上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我们用眼泪为它消炎,却要靠它自己来愈合,但不知需要多久。享受幸福,勿忘灾难,这是对的。
年夜饭,爱人在煮饺子,女儿则急着要我带她放鞭炮。爆竹声里辞旧岁,这或许是她一个新的兴奋点。吃着饺子,想着不知道父亲今年该怎么祭天祭祖。
小时候在农村,年夜饭的时候,母亲煮着饺子,大姐总要高声问一句:“生了吗?”母亲则回答:“生了!”这一问一答,实际上是借问饺子是不是升到水面上(也就是熟了没有),来寄托对父亲升官的渴望。父亲则在院子里放上一堆麦秸或豆秸,一旁放上个小案子,上摆着一杯酒、一炷香和一盘新出锅的水饺。父亲燃火、焚纸、酹酒、叩首,我静静地看着,直到父亲叫我也叩几个头,便点燃爆竹。我们称之为“发纸”,也就是一种祭祀。“发纸”的习俗大概源自山东老家吧,曾祖传给祖父,祖父传给父亲,一直就是这样。传到我这一代,就住到城里,不能继承下来。2008年父亲卖掉了平房,搬到楼上,没有了院子,大概不能“发纸”祭祀了,就把这个习俗记在心里吧。
年夜饭的饺子馅儿里,往往包上糖球、硬币和煤块儿。吃到糖的,一年甜蜜如意,吃到硬币的就会发财。而吃到煤球的,大概就要倒霉,也有说谁吃到煤球谁就是黑心之人的。后来过年包饺子就不放这么丧气的东西了。